香港文學|文具的宿命哀歌:從閃亮到褪色,再到被遺忘於抽屜裡
text/唐睿@《香港文學》 · photo/iStock · 2024-05-28

據說,在吉卜力美術館的一張桌子上,放了一個裝滿短鉛筆的大罐。乍看之下,都是些短得不能再用的鉛筆,但如果仔細看,就會發現,這些鉛筆兩頭都被削尖,看來並不是「一支」,而是由兩支短鉛筆接合而成的鉛筆。
上一次看到這種接合的鉛筆,已經是小學時代。它們由兩支短得難以掌握,相同或不同品牌的鉛筆所合成,接合的地方有時是用幾口釘書釘釘牢,有時則是用透明膠帶纏上幾圈,有時更是兩種方法的混合,在釘書釘外面還會再纏上一圈膠紙,好讓兩支鉛筆既能牢固連合,又不至紥手。

現在的小學生如何,已不太清楚,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每逢開學,孩子們似乎都會有一種需要正襟危坐的莊重自覺。
一切都能夠重新開始。
無論你是成績遠遠落後於人,或者再頑劣的同學,都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去年留在手冊上,傾注了老師各種憤懣和激動之情,筆力幾欲貫穿紙張的種種警句,都似乎可以一筆勾銷。取而代之的,是一本雪白的手冊,訴說着純潔之可貴,並提醒你為時未晚,回頭是岸。至於習作簿裡的奶黃色紙張,也彷彿散發着新鮮芝士的馥鬱氣息,教你不好意思,在開首幾頁留下歪斜的筆迹,以免它們像霉菌一般,在這些嬌艷欲滴的本子上蔓延。你是那麼珍惜,那些仍泛着彩色油墨味道的課本,不忘為他們裹上一層透明或磨砂(偶爾還帶有暗花)的外套,好讓你在行差踏錯的時候,可以不留痕迹地,拭去每個污點。

各種文具就更不得了。
Radar或Mono的柔軟橡皮,都難得拉直起筆挺和尖銳的邊角,抖擻精神;三支紅黑漆面,燙有金字的中華牌鉛筆,經過雙孔長方盒的筆刨開光,都一一亮出了流線型筆尖,任筆盒裡專門用來套筆的橡筋繩圈如何束縛,仍難掩它們躊躇滿志的神色;至於暗藏在筆盒底層的圓規呢,其奪目的鋒芒,替你惹來了多少同學的艷羨目光,乃至風紀的恫嚇,再帶返嚟就沒收,老師說,今年還未教授三角度數,再看到量角器或者圓規,物品的命運就會跟去年沒收的太陽能計算器相同。
那是誰的太陽能計算器呢?
事物總難免,滑進那帶鎖的抽屜,然後悄然無聲地褪色。

那些柔軟的橡皮擦,到了學期中,就變得蓬頭垢面,運氣好的,雖保留了一圈寬鬆的紙套外衣,也少不免衣衫襤褸;運氣不好的,則在無所事事的時節,被戳上了許多筆洞,慘不忍睹。至於那幾支中華牌鉛筆,一支,早已不知所終;其餘兩支,俱已矮了幾截,各有各的難堪境況。被尺子削去漆面的那支,露出了鮮肉色的木質,活像拔去羽毛,懸在活雞攤的鮮雞,手感粗糙,不想再用;至於橡皮擦頭斷了,被啃掉了銀色金屬圈的那支,則因為太短,難以固定在手攪式削筆器上,一俟筆芯鈍得不能接受,就可以正式宣告退役。
用刀子削一下,再跟另一支短筆接合一下就能用。

母親削筆的神情,就跟她鼓足幹勁,陪你寫作業的時候別無二致。那參差不齊的筆和潰不成型的筆桿,跟她殘缺不全的教育背景,交織出一種無以名狀的悲哀,以致你不得不編個藉口,逃到街上。
這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呢?
那天,當你在母親的家裡,看到孩子在塗寫一本奶黃色紙張的本子,才發現,竟然有這樣的一個抽屜,存放了一疊仍然在等待你記起的本子,以及一罐來不及被你想起,就耗乾了生命的水筆。
你將會愈來愈懷念,那支被丟棄了的接合鉛筆。

關於《香港文學》:
創立於1985年1月,為香港歷史最悠久、業界知名度最高的文學月刊。以香港為基點,團結華文世界作家、讀者,樹幟華文文學地標。
Thanks for subscri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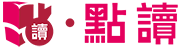
您提供以下所需要的個人資料,即表示您已閱讀並同意《點讀》的《私隱政策聲明》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並同意 《點讀》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以作訂閱《點讀》的電子資訊之相關用途。
如有需要,您亦可以隨時取消訂閱或修改您的個人資料。若有疑問,請電郵至 read@shkpreadingclu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