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挖掘城市記憶:那些藏在西邊街板間房的擠迫、混亂和煙塵
text/王良和@《香港文學》 · photo/iStock · 2024-06-20

1
你問,還記得西邊街12號的房子嗎?你說那時年紀太小,裡面有多少個房間,都記不清了。
我當然記得。房間只有一個,就是我們住的那一間。爸爸說過,七十幾呎,左邊一張碌架牀,我、家珠睡上格,家成、家愛睡下格;右邊的雙人牀,爸爸、媽媽、家寶、你和家齊,就擠到一起睡。兩張牀之間只有一張摺檯,天花板吊著一個燈泡。衣櫃?沒有衣櫃,碌架牀和雙人牀下,各有兩個衣箱,就這麼多。
那裡本來是沒有房間的,伯伯為我們在大廳間一個房間,給我們住。我們從鄉下來到香港,原本住在西邊街4號的閣仔,L形,爸爸、媽媽、家珠、家寶睡一張牀,牀邊掛一幅布簾;我和家寶,晚上翻開帆布牀睡,睡醒就收起來。壓死家寶?不會啦,她不是BB了,都三歲了。你和家齊還未出世。後來打風呀,甚麼風?對了,就是溫黛。2號的房子倒塌,整個騎樓都不見了。警察來拍門,說我們的房子隨時倒塌,快點走。那晚我們住進了對面的七號差館,整個差館都是人。打完風,4號變成危樓,我們就搬到12號伯伯家裡。伯伯?爸爸幫他打工的呀,見我們沒有地方容身,就在下層間了一個房間給我們住,房租不貴。大家都是紹興人,互相照應。伯伯一家住在閣仔,還有徐舅舅一家,也住在閣仔,他們都沒有房間,夫妻拉上布簾,孩子打地鋪,擠著睡。地牢是做年糕、蛋糕的工場,伯伯在地牢間了一間房給李師傅,他們的房間只有一個窗,對著天井。是呀,我們家九個,伯伯家十個,徐舅舅家六個,李師傅家七個。三十幾人怎麼住?就是這樣住呀,住不下也得住,還可以住到哪裡?怨,當然怨,我們本來在鄉下住得好好的,鄉下的木屋不大,都比這裡大,兩層都是我們的,在上層睡覺,在下層吃飯。我和家珠剛來時同阿媽說了好多次,不喜歡香港,要返鄉下。

2
長長的魚缸外常常站著一個穿汗衣、短褲、拖鞋的男孩,目不轉睛望著游來游去的魚。那些魚的身上散發奇怪的、好聞的藥香。水裡有時暈暈晃晃的盪來一個移動的人影,有時是一隻不動的、微微抬起的腳,朦朧的手影打著一個一個小小的白圈。他感到水涼涼的,升起密簇簇的綠色傘子水草,隱秘的角落,水底的沙石絲絲沙沙生出數不清的好看的小氣泡,湧到水面聚散消失。一個瓦煲的蓋子冒出白色的煙。一條身上有四條黑間的小魚,從煙霧中游向他,口裡呵出更好聞的藥香,他貪婪地猛吸鼻子。
每次經過這裡,他都不禁停在大魚缸前,聽身邊也在看魚的大人教導身旁的孩子說,這是甚麼魚,那是甚麼魚。他漸漸認識那些魚的名字:黑神仙、接吻魚、紅蓮燈、玻璃貓、黑裙、斑馬、四間、紅鰭鯽。他最喜歡黑神仙和接吻魚。那些黑神仙都很大,背鰭、腹鰭、尾鰭都是黑的,胸下垂著兩根長長的鬚,一隻隻三角形風箏,緩緩地、優雅地在天水間飄浮。最有趣是接吻魚了,粉白粉白的,像小豬,豎著半透明的柔軟背鰭和腹鰭,老是不停噘啜著小嘴。有時一啜一啜吻著魚缸的玻璃,有時兩條接吻魚噘張著嘴,嘴對嘴,一啜一啜的吻完又吻。他總是等待兩條迎面相向的接吻魚,期待那一刻……啜啦啜啦!……噘張的小嘴,啜合的小嘴……。近了……近了……。

「嘩!明星呀!」
「家興,有明星睇呀!」
被接吻魚迷住的家興,忽然驚醒,拖鞋啪噠啪噠的跑離了掛著長長招牌的「趙醒楠」,跟著姐姐、滿街小孩跑向停在七號差館對面的橙色廂形車。他以為看到的明星是陳寶珠、蕭芳芳,或者曹達華,卻聽到大人此起彼落大喊:「胡楓呀!胡楓呀!」
他不知道誰是胡楓,但見許多小孩追著這個明星,有的攤開手掌,有的伸手抓他的恤衫。他不斷聽到有人說:「胡楓,給我一百元!」
「十元!」
「一千元!」
胡楓親切地笑著,十分慷慨:「好好好。下次畀你,下次畀你……畀你。」
「你記住我呀!……一千喎!記住我呀!十元……一百元!……」
胡楓上了車,胡楓的車關上了門,胡楓的車開走了。萬千小孩潮水般湧向自己的家門,興奮地告訴媽媽或者爸爸或者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姨媽姑丈叔叔嬸嬸舅父舅母:胡楓答應給我一百元……一千元!家興好快樂,總是念念不忘胡楓──總是等待那輛橙色廂形車,總是對人說胡楓欠他一百元。

3
凌晨一點半,家珍在昏黃的燈泡下,凝神注視著眼前的假人頭,動著鈎針。
今天早上,家珍買了一個長麵包,五毫子,很大的一個麵包。早上喝暖水,吃半個;中午吃半個,喝暖水。工友中午喜歡到外面吃飯:「阿珍,不要吃麵包啦,去祥記吃雲吞麵、魚蛋粉。」
「我喜歡吃麵包,飽啦。」
家珍很珍惜鈎假髮這份工作,比起在塑膠廠啤塑膠、在紗廠駁線,真是好得多了──天天在紗廠站著,眼前是無數顫動旋轉的木棒、綑綑白紗,一柱一柱燭台鋼棒規律地升降,整個世界只有機器嘰嘰札札的聲音。快手快腳,快手快腳,家珍不斷提自己,把兩條紗線縛在一起,快手快腳──站了七天,在嘰嘰札札的冰冷的機器聲中,頭暈暈,滿眼白的紗線一黑,快手快腳──腿一軟,家珍在精力充沛、生產力旺盛的工廠中暈倒了。阿香帶她去大馬路看梁孟雄,醫生檢查後,說她身體裡的血,比別人少一半──嚴重貧血。打了一星期補血針,調養好身體;紗廠的工作不能再做了,做了七天,一毫子工資都領不到。怎麼辦呢?她是大家姐,下面還有許多弟妹要吃飯,總得想辦法。阿水認識的一個裁縫師傅說,女兒在九龍的工廠鈎假髮,收入不錯。她的女兒介紹家珍進廠,家珍做熟手了,又介紹家珠。家珍下班,總會把假髮帶回家鈎到半夜三更。

許多年後,家興和家珍聊往事,總是說有一個畫面揮之不去──半夜醒來,朦朦朧朧的暗黃燈光下,總看到一個木人頭被鋼鐵鎖住、被一個黑色的網牢牢套住,大家姐靜得怕人,凝神盯著眼前的人頭,手裡的鈎針在人頭網眼間搖捲拉扯,就扯出一個披頭散髮、沒有五官的女鬼──好像姐姐帶他到太平戲院看電影,電影院好黑好靜,熒幕好黑好靜,陰森森的荒野幻現一個棺材,棺材的蓋忽然高高彈起,無聲無息飛出一隻幽藍衣袍的殭屍,帶血的眼睛,張口露出長長的獠牙,長袖飄飄帶著寒風直直飛過來,愈來愈近,愈—來—愈—近,披頭散髮──而此時家珍一邊鈎假髮,一邊看到──
爸爸不停咳嗽,咯……咯……。
張口收縮的喉嚨,猛烈挫動的頭和胸背。
小小的淺綠塑膠桶裡,一攤一攤爆開的、又紅又腥的鮮血。
面色蒼白,面頰凹陷,胸骨凸出。
爸爸跪在醫生面前,求醫生救救他:我還有七個兒女要養……我不能死!
爸爸住進律敦治療養院,很久很久,爸爸,還未回家。

家珍的鈎針又使木人頭生出幾條長長的假髮,假髮愈來愈長,黑蛇似地游動,愈來愈長,愈去愈遠,一叢一叢捲住門鍵,拉開門,轉彎,游到西邊街10號的籮斗舖,靈靈巧巧穿過高高疊起的籮筐、蒸籠,把潮州婆三十歲的兒子阿偉一針一絲、拐彎抹角的勾進來。阿偉笑笑口:「鈎假髮好得意,怎麼鈎的呀?」
第二天,阿偉吃完晚飯,無所事事,又走來,進門笑笑口:「鈎假髮好得意,有男人鈎假髮的嗎?」
第三天,阿偉吃完晚飯,有所事事,借頭借路走進西邊街12號,進了房門笑笑口:「鈎假髮好得意,教我鈎幾針,可以嗎?」
家珍左手捏著一圈假髮,右手拿著鈎針,開始教阿偉鈎假髮:「把針頭穿進網眼,擰一擰手柄,這樣出來,注意要把保險一起帶出來呢──像這樣,把保險帶出來了,就把針頭鈎住左手的頭髮絲,一次鈎幾條,拉回來的時候,保險會自動閉上,鈎住的頭髮就不會亂了,然後這樣拉……」阿偉高興地接過家珍的一圈髮絲、鈎針,坐近來,家珍感到甚麼地方呼出了一絲溫暖的氣流。
星期天早上,阿偉打開家門,想約家珍去多男大茶樓飲茶,吃雞球大包;遠遠看見家珍坐在七號差館門外的石板上,大腿間放著木人頭,套著黑網,左手捏著一圈髮絲,右手動著鈎針,無意間往這邊望過來。
星期天的早上,天空一片蔚藍,晴陽朗朗。

4
七號差館是家興的小小樂園,入口不遠處的圓形草坪,常種大紅花,家興和其他小孩只管叫蜜糖花,因為含苞待放的大紅花,拔掉綠色的花托,吸啜花底,往往啜出香甜的蜜,啜完,把瘦瘦長長、像捲煙的火紅花苞丟在草坪上。夏日的草地常有蜻蜓,收捏膠袋中段,張開袋口,小心翼翼,走前,慢慢俯身,不難罩住在草間休憩的紅尾蜻蜓。草地右邊盡處有高高的蒲葵,可以抓住巨大的扇形葉盪鞦韆,旁邊低矮的方形小屋,爬到屋頂跳下來,十足小飛俠。在大門口站崗的差人,很少攔住外面的小孩,不准進去玩。偶然,住在警察宿舍的孩子,不知為甚麼和西邊街的小孩吵起來,隔著馬路互罵,詈罵的稚氣石片飛來飛去,無人受傷;很快又和好,中秋節晚上,提著紙摺燈籠、自製的柚皮燈籠、月餅盒燈籠,在七號差館的草坪間你追我逐、喊著「借火」,遠看像許多一閃一閃的螢火蟲,在幻夢的蔦蘿幽樹間說著蟲言的光塵,此呼彼應,轉瞬即逝。
清晨的西邊街總有一股淡淡的屎尿氣息──光是12號,三十多人的屎尿,四家人四個馬桶,深夜一個一個端到門外。子夜,倒夜香的木頭車,殼拓殼拓來到門前,又殼拓殼拓走了。是甚麼人幹著倒夜香的行業呢?男人還是女人?夜香是怎樣傾倒清理的呢,要不要用刷子?三更半夜,累不累啊?而家興累了,睡眼惺忪,迷迷糊糊聽到四姐姐走出房門的聲音──把自己家的巨大馬桶端到門外,天亮收回來。夢裡夢外,他習慣了打開蓋子合上蓋子、甚麼東西高低碰撞、殼拓殼拓漸輕漸細漸漸荒涼的深黑聲音,帶著令人昏昏欲睡的糞尿的疲累。而每天清早,他總會被噓噓的、咕嚕咕嚕的水聲叫醒──牆壁的水管醒了,開始一天的工作,要飲水清洗喉間腸道一夜的積穢;天井牆外,鏽迹斑斑的水管也醒了──有人刷牙,刷刷刷,咕嚕咕嚕,吐……吐……,傾呤傾呤,沙……沙……,一潑一潑的,空氣中薄薄飄來黑人牙膏會說話的亮白薄荷香氣──起牀囉!家興打開門,第一件事就是走到門外馬路邊小便。開著白色私家車的司機,從海邊轉入西邊街,開始上斜路,看見右邊馬路旁一個五、六歲的小孩拉下褲子,一條彎彎小水柱,射中一張躺在地上的紙──他笑一笑,然後專注擋風玻璃前的街道車況,小孩向後刻刻移動的身影在眼角流逝──家興低頭一看,拉高褲子,蹲下來,撿起一張啡色的、濕濕的鈔票,上下左右四角都有一個「5」──一個女人側臉坐著,盤著螺形高髻,好像戴上了假髮──他左右瞧瞧(執到寶,問天問地攞唔到),轉身,進屋交給媽媽。媽媽一邊誇他一邊笑得好開心,當天就買了一隻雞──昨天米缸沒有米,媽媽寒著臉等爸爸回來,今天一家竟然有雞吃。他知道自己的尿還可以治病──爸爸說哥哥總是咳嗽,要喝童子尿醫一醫,就把一個漱口盅放到他的褲子前,叫他把尿屙到漱口盅裡給家成喝。家成幫他沖涼的時候,他聞到哥哥的口有尿味,嘴角不受控制地顫動。

門外的斜路,時常有小孩玩跳飛機、橡筋繩、擲公仔紙、撿幾粒小石玩搲子。左鄰右里捉到灰灰黑黑的坑渠大老鼠,用長長的黑鐵鉗夾著長方形的銀色鐵籠提到門外,淋火水,點火。小孩子停了玩耍,圍過來看。火一亮,老鼠吱吱大叫,在籠子裡狂奔,撞得籠子突突顫動──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吸……吱──火光熊熊時,籠子只有火的聲音和帶著火水味的白煙,沒有人拍掌,只是靜靜地嗅著火水鼠肉的燒焦氣息。有人一邊看一邊喃喃自語:「牠不死我們死,鼠疫呀,太平山街死了多少人!」
5
家珍和籮斗舖的阿偉結了婚,不鈎假髮了,天天坐在籮斗舖裡,很少笑,低頭默默做籮斗,把竹篾捲起來,釘成不同大小的圓篩,加紗網,一個一個疊高。
「阿珍……你細佬……哎呀!煙塵呀!」阿珍放下手中的竹篾,紅著臉衝到門外。只見弟弟肩上披了紅布,用晾衣的木夾子在胸前夾著布領,又爬到10號門口右邊的石屎高台,扮小飛俠跳下來。「煙塵呀!」她的家婆老是不悅地說「百厭」──「百厭星君」終日跳跳紮,弄得一街煙塵,吃飯時見到他尤其憎惡,一雙筷子夾到飯碗下,嘴唇油亮亮,尖削削,唱潮州曲一樣「煙塵呀!煙塵呀!」然後無意識地搖著頭:「冇家教!」阿珍最恨聽到這三個字,鼓著一肚子氣撲前去追打弟弟,邊打邊罵:「叫你不要跳還跳!害人精!」

晚上九點半,阿水放工回家,偶然會教兒子寫字。從南貨店帶來的荔枝,剝去胭紅粗糙的果皮,小小的、空落落的昏暗房間就升起一陣荔枝獨有的甜香。阿水把荔枝微微透明的柔軟白肉放進碗中的鹽水裡浸一浸,水灕灕的放進兒子口裡。一點點鹹,滿口濃濃的香甜,這是擠在西邊街12號小房間這一家人記憶中最美好的瞬間。
「爸爸,為甚麼吃荔枝要點鹽水?」
「吃荔枝容易上火,點了鹽水可以降火。」
阿水認得的字不多,他連寫一封信寄給家鄉的親人都覺吃力。吃完荔枝,他要兒子寫字給他看。兒子拿出薄薄的簿──他終於有書讀,可以學寫字了。他已經記不清央求媽媽多少次──媽媽在門外晾著衣服,把一條長褲、兩條長褲穿進長長的竹竿,把一件花衣、三件花衣掛到竹竿上,用木夾子夾住衣服兩側,重重的、高高的用鐵頭木叉叉到騎樓的天花鋼架。他又拉著媽媽的衣角:「別人都有書讀,為甚麼我冇書讀?我好想讀書。」媽媽總是說「學費」,然後回到房間,晾完衣服坐在牀上穿膠花──而他終於有書讀,可以學寫字了。爸爸總是要他坐端正,線條寫歪斜了,爸爸用擦紙膠擦掉,要他一筆一畫寫好:「我和你媽媽在鄉下是耕田的,只會拿鋤頭,只會種菜,不識字,沒有盼頭;你要勤力讀書,爭爭氣氣,不要學壞。」
阿香用力把一個頭擰進頸部的圓孔裡,再用力擰接兩隻手、兩隻腳,把最後一個肢體完整的塑膠公仔放進大布袋中,明天連拖帶拉交回第二街的塑膠廠。阿香揉了揉大拇指,打了一個呵欠,累得睡著了。阿水仍在教兒子寫自己的名字,問他知不知道自己姓甚麼。兒子快樂地學著,鉛筆在紙頁的井田中沙沙行進、挖掘,歪歪斜斜的,一筆一劃,有了雛形:祈—家—興。
門外又傳來木頭車殼拓殼拓的聲音。天井老鼠叫:吱—吱吱。

關於《香港文學》:
創立於1985年1月,為香港歷史最悠久、業界知名度最高的文學月刊。以香港為基點,團結華文世界作家、讀者,樹幟華文文學地標。
Thanks for subscri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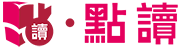
您提供以下所需要的個人資料,即表示您已閱讀並同意《點讀》的《私隱政策聲明》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並同意 《點讀》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以作訂閱《點讀》的電子資訊之相關用途。
如有需要,您亦可以隨時取消訂閱或修改您的個人資料。若有疑問,請電郵至 read@shkpreadingclu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