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佢點讀|還以為人生是場遊戲?可重新玩過?少年,你真的太年輕了!
text/嚴邊 · 聲演/樂善堂王仲銘中學:周佩瑩、林金弘、吳穎涵、盧雋逸 (《點讀》廣播劇比賽--尋找「聲探」的故事得獎得主).photo/iStock · 2022-02-28
text/嚴邊 · 聲演/樂善堂王仲銘中學:周佩瑩、林金弘、吳穎涵、盧雋逸 (《點讀》廣播劇比賽--尋找「聲探」的故事得獎得主).photo/iStock · 2022-02-28

*本書選段以廣播劇形式演繹,與原文稍有不同*
《死亡入境處》
作 者:嚴邊
出版社:天行者出版
第一約 新人上任(節錄)
重刷首抽!人生只不過是一場遊戲,有甚麼大不了,死亡不就可以把人生化整為零嗎?遇到不堪的命運,重玩一次吧!遇到痛苦與不幸,重玩一次吧!遇到不願面對的困難與壓力,重玩一次吧!「做人,最緊要開心」,何必和自己過不去?生命是自己的,人永遠是自私,我的人生用不著別人來管,別人也管不著,所以我選擇自殺,了結我滿是錯誤的生命。死後我不再聽見世間對我的百般唾罵,不再看見旁人對我恥笑的嘴臉,等候我的只有一片寂靜與虛無。
再見,再也不見。
我拿出背包內的錢包,裡面沒有分文,唯一的十元硬幣也花在前往這裡的小巴上。錢包裡僅僅有一張破舊的身分證,我卻認不出證上的自己;內裡還有一張很多年前簽下的器官捐贈卡,但今天大概派不上用場,因為我選擇了一個沒有人會發現的死法。
我從崖邊一躍而下,沉入漆黑如黑洞的大海中,但大海並沒有像一個慈愛的母親般容納我這個不速之客。跳海的衝擊力一瞬間沖擊腦袋,意識頓時喪失,兩三秒後,猛烈的海水已經湧進我的口鼻。本能地,我拼命的掙扎,四肢像掉進滾燙熱水裡的青蛙般拼力擺動,但徒勞無功。窒息的恐怖遠遠超乎我的想像,我無法閉氣,喉嚨亦不聽使喚,咕嚕咕嚕地吞水,直到內臟也注滿了水。越是掙扎,越往下沉,彷彿地獄中有無數隻手緊緊拉住了我的雙腿,用力地往下扯。我的身體離海面越來越遠,墮入陽光無法抵達的深淵。恐懼,痛苦和絕望互相交織,直到我徹底喪失意識,成為黑暗的一部分。
啊,真好,終於死了。
雖然我說不出這一句。
當我再次醒來時,發現眼前一片明亮的白色。難道自殺的人也能上天堂?我想應該沒有這般美好的事吧。
「我沒死成嗎?」口中不自覺地嘆息了一句,不禁失落。
「跳海不死,你以為你是某電視劇的主角嗎?向來跳海致死率高達九成八,而你當然不是甚麼奇蹟,甚麼蒙受上帝眷顧的人好嗎?」
事實請不用說出來,讓我留一點幻想空間。
我當然知道像我這樣罪孽深重的人不會得到前往天堂的入場卷。
坦白說,死法各式各樣,為了選擇成功率高又不影響他人,方便又得體的死亡方法,我可是做了很仔細的資料收集。
而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被人發現。
請讓我安靜地離去,像我不曾在這世界上存活過。

因此經過重重考慮,我最後選擇了跳海。跳海死亡率高,加上自身不懂游泳,死亡的成功率可謂百分之一百。只要我背負纍纍石頭沉入大海,我的遺體便不會被發現。如無意外,我的肉體會成為魚類的食糧,我的白骨會化作珊瑚的依靠,我的一切痕跡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生物本從大海而來,而我今天回歸大海,回歸自然,這不是最合理的死法嗎?
不過,我始終低估了死亡的痛苦啊。
回過神來,一個人影終於清晰地浮現,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一身全雪白西裝,配上白領呔,卻又出乎意料地合適。他西裝的袖子上有一道深紅色的條紋,格外搶眼。
我猜不到他的身份,因為地獄裡應該沒有天使。
「既然我死了,這裡是地獄嗎?你又是誰?」
「這裡是異於人間的四維空間,稱為死亡入境處的地方。而我是入境處的守門人,專責批准已死之人入境和核對身份及死因,責任重大。」他稚氣的臉上泛起一絲不明的驕傲。
「不就是關員嗎? 」 我坐起來,仰望那少年,不自覺地表露出少許輕視的神情。
「喂,說話放尊重些,現在關員很失禮你嗎?這可是一份好工作,我申請了五十多次才能從管制部調至審核部,你根本羨慕不來!」不知他哪裡來的怒氣,迎著我的臉衝過來。
「我沒這意思。」真是自作多情,我壓根不羨慕他,誰想死後也要工作?特別是我這種極度厭惡工作的死廢青,消失便是蛀米大蟲對社會的唯一貢獻,要是再逼我工作,我寧願再死一次。
白西裝少年雙手叉腰,擺著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真讓人受不了。
「含羞草,我來負責吧。」旁邊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見我不耐煩的樣子,煞有介事地轉過頭來。他從含羞草的手上接過文件。
甚麼,這個臭小孩叫含羞草?可他一點都不「含羞」。
「過門都是客,人家初來報到,連自己在哪裡都搞不清楚,給點耐性慢慢解釋吧。」 他看不慣含羞草的語氣,對他加以教導。看見含羞草一時語塞,我心裡頭偷笑著。
文質彬彬的眼鏡男同樣一身白西裝,但袖子上有兩道深紅色的條紋,看來是這個含羞草的上司,而且面目慈祥,笑臉迎人,應該較易說話。
「我有很多問題,但不知從何說起……」
「明白,由於你是自殺身亡的,和其他陽壽已盡的人不同,所以會安排較特別的死後處理。這樣吧,你兩天後前往地下四樓的人事部,那兒會有一場入職講座,屆時你便能理解這一切了。」
我越聽越迷糊,甚麼特別的死後處理,不就是上天堂或是下地獄,或是輪迴轉世嗎?難道還有其他出路?甚麼入職講座,甚麼人事部?我是在做夢吧,為何死後的世界和人間沒甚麼兩樣?我可不是剛從大學畢業投入社會的新鮮人呀!
「不過你現在先前往地下三樓的支援部休息一下吧。」說罷,眼鏡男轉過頭,一邊繼續處理他手頭上的一疊文件,一邊和含羞草說:「我要去人事部一趟,你有問題的話便問其他同僚吧。」含羞草點點頭,故作乖巧。待上司走後,他朝我做了一個鬼臉,便匆匆離去。
果真是個臭小孩!
我從床上下來,環視四周,發覺四處都是病床,仍然一片雪白。我莫名打了一個冷顫,大概是因為眼前的環境詭異得很吧,既非天堂,也非地獄,卻像人間。

我發覺我正穿著一套病人的制服,和大部份徘徊在這無邊無際的病房的人是一樣的,但亦有小部份人身穿日常的便服,和普通的路人別無兩樣。我想兩者都是死去的人,只有身穿白西裝的才是這裡的職員。
雖然我厭惡社交,但按這個情形,我也應該跟身邊遭遇同樣處境的人打個照面。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想必其他人也和我一樣懵懂,不知就裡。但當我發現左邊躺著一個對著天花念念有詞的老人,右面又是個正在啕哭大叫的男人,還有一個四處奔走,喊著他人名字的少女後,便打消了閒聊的念頭。
沒辦法吧,唯有先跟從指示,見步行步。我依照地面上前往支援部的路標走了十分鐘,終於看到出口的標誌。面前仍有一堆人正在排隊等候升降機,猶如繁忙時間的地鐵站出入口。
人山人海,居然只有一部升降機?
升降機旁邊有一個警告牌,表示「此升降機只能前往地下三樓,禁止往返」,甚麼鬼?單程升降機?有去沒回的旅程讓我有點卻步。
剛好,有一個同穿白西裝的老婆婆發現我遲疑的步伐。
「不用怕,年輕人!人遲早也要走到這一步的!」她的謎之鼓勵令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應。
「啊,不好意思……請問我去了支援部後應如何前往人事部?」
老婆婆一聽,臉色馬上一變,輕輕一嘆,別過臉道:「看不開的年輕人啊,真可惜……」
「請問……」
「啊,老人家老是恍神。小伙子,你現在還不能用職員專用的升降機。你記住,支援部有兩部升降機,一部是前往地下五樓訴訟部的單程升降機,另一部是前往地下四樓人事部的,特別給予新入職的人員使用。由於你是後者,被分派到所屬部門後,便會獲得一套職員制服,身穿制服的職員才能夠使用後街的職員專用升降機,明白嗎?」
婆婆一指第二個路口,地上有一條白色指示路線,前往另一個未明的深處。
雖然我仍不清楚自己為何成為新入職的職員,但老婆婆對路線相當清楚。
「明白,謝謝妳。」眼前的老婆婆大概七十多歲,但思維仍相當清晰,我心中不禁佩服。「請問妳怎樣稱呼?」我不善言談,說話總是文縐縐的,甚是怪異。
「哈哈,大家都稱呼我杏婆婆,在支援部工作也有八九年了。」
「支援部的?但這裡不是支援部啊?」雖然我不知道我身處那個部門,但肯定不是地下三樓的支援部。
「通常在支援部工作的都是些老弱傷殘,負責支援各部門,擔任跑腿,人群管理之類的工作。而杏婆婆我是在地下二樓審核部當引路人員的。」杏婆婆微笑道,看來挺滿意這份輕鬆的工作。這時,我才發覺她的袖子有一條平和的綠色,與婆婆與世無爭的氣質甚為配合。

「原來這裡是審核部啊……」這個答案稍微撥開我心中的迷霧,但我仍像管中窺豹,看不清這個陌生地方的全相。「那審核部是負責……」話音未落,我已被後面排隊的人推進升降機裡,只見杏婆婆對我揮揮手,叫道:「遲些見啦,小伙子!」
升降機雖然寬大,但人們蜂擁而至,內裡如同沙甸魚罐頭般擁擠,使我根本透不過氣來。
「叮咚,地下三樓支援部。」廣播聲和平日在地鐵聽到的沒甚麼兩樣,大概只差一句「不要超越黃線」。
哈……這一分鐘像過了一年似的。我大口大口呼吸,不過也就是做做模樣,因為想必在這個四維空間裡也沒有空氣。
「請注意,剛抵步人士請前往中央分流處排隊拿籌號。請注意,剛抵步人士請前往中央分流處排隊拿籌號。請注意……」
廣播連番響起,提示我們這群新來賓下一步要做甚麼。不過,中央分流處之類的也太像醫院的急症室大堂吧,難道也需要等六七個小時嗎?
說時遲那時快,又一段廣播播放:「新來的人士請注意——現時輪侯時間為四年又三個月。」
噗!甚麼?四年又三個月?這也太離譜吧!
「等政府龕位也是差不多時間,等也等慣了。」
「我等死也等了十多年,不差那一點時間。」
一大堆人坐在遼闊的大堂靜靜等候,等待四周的顯示屏上出現他們手中的籌號。百無聊賴,突然,我有點慶幸自己將會有份新工作了。看來我還是乖乖等兩天,然後到人事部報到吧。
我坐在大堂的一角,挨著樑柱小憩一會。忽然,我聽到一把熟悉又尖銳的女聲焦躁地說話,「請問你有沒有看見我男朋友?他叫黃一帆。」
是剛才在審查部四處找人的那個少女。她又再次向身穿白制服的支援部人員詢問。
「對不起,我不清楚。」一個老伯伯毫無懸念地答道。這是公務員一貫的答法。
「怎能不知道?我和他一起自殺的啊,我們還互相答應下一輩子也要在一起呀!」少女越說越急,急得連眼淚也出來了。
自殺?不是和我一樣嗎?
老伯伯應付不來這個難纏的少女,身邊的支援人員見狀,都紛紛前來幫忙。但少女情緒越見不穩,叫道:「你們說他可能到了地下三樓,我才找下來呀!現在又是甚麼情況?」

審核部的人把她當人球般推到支援部,想必支援部的人也是一頭霧水。
「小姐,你和你男友是自殺死的嗎?」雖然我不過剛抵步,但仍嘗試幫助支援人員釐清一下,畢竟剛才也得到杏婆婆的指路。
「對……對呀!」少女一看我伸出援手,雙眼發出希望的光芒,向我求救。
「你問他們也是徒勞無功,他們不會知道的。」
「那我該怎樣辦啊?」她見我為支援人員解圍,又開始失控。
「你先冷靜一下。自殺的人需要前往人事部報到的,你也聽過吧?」
她點點頭。
「這裡二三千多人,你能單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他嗎?不能吧,既然你肯定你的男友同樣自殺而亡,那麼遲些他也要到人事部,對吧?。」
支援人員也紛紛說是。
「其實我也要前往人事部的,要不然我們一起去吧,多個人好辦事。」我嘴上說著的,不過是安慰的說話。坦白說,我哪知道她的男友是否死得透徹?
她暗自思量,發覺也有道理,便安靜下來。支援人員見我擺平了事情,悄悄擺出了合十的手勢,以示感激。
我陪她找了個小角落坐下來。
她像得有點像少女模特兒嘉寶,但比她年輕,大概只有十六七歲。齊劉海直髮令她的臉顯得更小,加上五官精緻,甚是漂亮。
「你不要騙我。」她仍是徬徨非常。我明白,若是一對情人雙雙殉情,卻有一方死不去,那斷然是比死更慘痛的事。
「你別怕。」我下意識想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但頓時意識這對一個剛認識的女性並不合適,便立即縮手。「對了,你叫甚麼名字?」
「我不記得了,我只知道我男友叫黃一帆。你呢?」她不安地看著我。
「我叫……」咦,我叫甚麼?「我叫……」想不起來了,怎麼會想不起來自己的名字。我……
我馬上慌了。徹底慌了。
我回想一片自己腦海裡所有的記憶。
我今年三十歲,爸爸早年因為意外去世,之後我和媽媽相依為命。攻讀大學後出來社會工作,但不知為何,每份工作都做不長。後來經濟轉型,電腦工程這行業不再吃香,我也失業了。手持大學學歷的我,不甘找一份較低薪酬的工作,但高薪酬的工作又沒有我的份兒。長期失業的我變得更自卑,也不願外出社交聽他人的閒言閒語。為了不連累媽媽,我搬出去住在只有一百呎的劏房,靠著媽媽的接濟苟且活著,成為人人避之則吉的隱蔽中年。最後,在無止境的孤獨下,我選擇自殺這條不歸路。而我的名字是……
糟了,我想不起來!

Thanks for subscri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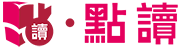
您提供以下所需要的個人資料,即表示您已閱讀並同意《點讀》的《私隱政策聲明》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並同意 《點讀》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以作訂閱《點讀》的電子資訊之相關用途。
如有需要,您亦可以隨時取消訂閱或修改您的個人資料。若有疑問,請電郵至 read@shkpreadingclu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