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佢點讀|愛上拳擊就是奮不顧身地揮灑汗水,多傷多痛都永不放棄
text/凌望 · 聲演/Derek Poon (《點讀》「新星大募集」好聲音銀獎得主).photo/iStock · 2022-06-30
text/凌望 · 聲演/Derek Poon (《點讀》「新星大募集」好聲音銀獎得主).photo/iStock · 2022-06-30

《拳鋒交錯的距離》
作 者:凌望
出版社:天行者出版
第一章 擂台
Rocky 的「Gonna Fly Now」,在擂台旁的喇叭裡播出,因為喇叭是便宜貨的關係,樂器聲幾乎都是糊作一團的。
拳擊手在實戰訓練時,一般都會將音樂剪成正好三分鐘的長度;這樣就可以不必分神看時鐘,又能大概知道時間的流逝。
雖然「Gonna Fly Now」實際上並不怎麼適合這種用途,畢竟它的旋律聽起來重複性實在相當高,並不如某些曲目,能夠輕鬆地分辨目前在曲子的哪一段。
可是每一個拳館——甚至不用加「幾乎」二字在前頭——都會用這首歌作為其中一首訓練音樂。
而在旁邊的擂台上,兩個分別帶著紅藍色拳套的男子來來往往地交換著攻勢。
藍色拳套的一方看起來明顯比較年輕,但背上早已全部被汗水所浸濕,呼吸亦已經略見急促。
反觀紅色拳套這一方,雖然臉龐略見風霜、頭髮也帶些許斑白,但他發汗遠沒有藍方嚴重,呼吸也明顯平緩得多。
在音樂激昂的旋律中,兀然地出現了「滴滴滴」三響,那意味著一回合的三分鐘,只剩下最後的十五秒。
兩人聽見那三響之後,同時深吸了一口氣,展開最後一回合的攻防。

藍色拳套一方知道自己的體力已經不足夠支持自己在最後這一回合主攻,於是決定再 往後急退了一步,背脊直接倚著擂台的繩角,曲著身子,雙手標準地保護著自己的頭顎。
再撐十三秒就好。
他後退的同時,分神看了看懸在牆壁的電子鐘,鮮紅的數字在他往後急退之間,又無聲無息地跳了兩次。
帶著紅色拳套立於他面前的,正是當年那個向小男孩示範揮拳的中年男人。
而他,自然就是當年那個垢面蓬頭的小男孩。
相較當年,不再年輕的中年男人雖然添了不少歲月的痕跡,但其肉體經已沒有了當時那種鬆弛的感覺,目光也帶著銳利的精芒。
那一天的後來,馬頭——也就是那個中年男人,將那個髒兮兮的,名喚鄭護的小鬼收為徒弟。
經歷了身體成長得最劇烈的數年,鄭護本來就不矮的個子幾乎像是被扯長了一樣,本來不到馬頭胸口的個子,現在已經比他高出了不少,護在頭臉前的手臂更是長得出奇。
看到徒弟向著電子鐘那沒出息的一瞥,馬頭打消了本來想放他一馬的念頭,再往前踏了一步準備揮拳。
他的左足足尖用力點在略帶彈性的布製地蓆上,發出了「啪」的脆響,然後左足尖順時針方向往內一旋,推動左面身子,帶動左拳便往鄭護的下顎處刺去。
專注於防守的鄭護眼見師傅的直拳將至,用作防護的雙手肌肉也不自覺地繃緊了許多;而這有時候是很致命的——尤其在近身戰的時候。
搏擊運動所追求的,很多時候都與人類天賦的本能背道而馳;例如面對高速地往自己揮來的拳頭時不可以眨眼,就是其中一樣最簡單易懂的例子。
而緊張的時候將自己的肌肉繃緊也是人類自然不過的本能反應,但繃緊的肌肉同時意味著動作之間的切換會大大減慢,而這一切正在師傅的計算之內。
面對揮來的拳頭,在長年累月的訓練之下,正確的防禦動作早已變得有如反射一般,但鄭護在接下拳頭的一剎那間,立馬便心知不妙,畢竟這拳……實在太輕了。
事態發展至此,一切已成定局。

鄭護肌肉繃緊之下,腰腹處完全中門大開,懸於頭顎處的雙手根本不可能來得及回防。
師傳露出了淺淺的微笑,腹肌一捲,沒有揮出全力的左拳瞬間便扯回了左側,已往內旋的足尖順勢牽著左半邊身子往下一沉,就像一張拉滿了的長弓。
弓如滿月,箭如流星。
帶著赤紅色拳套的左拳以比剛才快上兩三倍的速度往鄭護的側腹處揮去,幾乎化成一道赤色的殘影。
既然來不及防禦——
拳頭及腹之際,鄭護拚盡全力呼氣,發出「噝——」的鳴響聲。
用力一呼之下,鄭護肺部裡的空氣淨空了大半;橫膈膜往上升之際牽動著腰腹處的肉往內收縮,好盡量卸去這一拳的打擊力。
即使身心已經準備好,拳頭及體仍是會帶來難以忍受的巨痛。
師傅的拳頭狠狠地擊中橫膈膜處,痛楚之下鄭護幾乎無法呼吸。
幾乎淨空的肺部熱烈地渴求著新鮮空氣,但橫膈膜幾乎完全無法響應鄭護的吸氣動作而正確地升降;就像是四圍的空氣被凝固了似的。
但這輪攻防仍未完結——一擊命中,師傅潛藏已久的右拳便又往鄭護下巴處揚去。
鄭護側腹處中拳,身體自然會不由自主地像是蝦米般往內弓,這時俯前的頭部正是絕佳的攻擊目標。
但鄭護側腹被擊中之際,眼神並沒有半點慌亂,只是立馬右拳往下一沉,然後往馬頭下巴處挑去。
兩敗俱傷絕對比單方面捱打好——再也簡單不過的道理。
馬頭明顯讀懂了鄭護的意圖,眼裡帶著明顯的讚許。
這種從死地中無意識地尋找勝機的直覺是沒辦法以鍛鍊獲得的,只能源自與生俱來的野性。
面對鄭護想要兩敗俱傷的一擊,馬頭卻沒有半點收拳的打算,肩胛處用力一押之下,拳速又再快了幾分。
兩人的下一著幾乎同時而發,在擂台上揚起了紅藍二色的流光。
「噹噹噹——」電光石火的一瞬,擂台旁的喇叭傳來明顯帶著廉價電子音的鐘響,示意著這回合告一段落。

而兩人的拳頭在鐘響的剎那間,如同時間被暫停一樣凝固在原地。
兩方的拳頭都離對方的下巴不到兩公分。
「休息一回合。」師傅看一看鐘,轉過頭便拉開擂台旁的繩子,離開了擂台。
鄭護小心地調整著呼吸,刻意延長呼吸之下,橫膈膜處一跳一跳的痛楚也慢慢地和緩了許多。
「老了、老了。」師傅漸漸步下擂台,脫下拳套隨便往外一甩,說道。
好不容易才緩過呼吸的鄭護看著窗外,外頭已是一片漆黑,但在燈光反射之下,明顯看到窗外掛滿了雨滴。
每逢風雨天,師傅都會變得很弱。
鄭護心道。
假如是平常的師傅的話,側腹處這一拳打實了就算沒有當場昏眩,也絕對沒有還擊的餘地。
雖然如今側腹處的痛楚依然久久未散,但相較於師傅往常的拳頭而言,絕對是輕上了許多。
「你的臂展沒有用盡,休息完練習一千次前手直拳。」師傅輕輕按著自己的右眼肚,道。
這就是師傅風雨天會變弱的原因。
馬頭曾經很強。
在現役的的數年間,他幾乎沒有讓出過香港的冠軍腰帶;甚至出身於拳擊界算是積弱的香港,卻有能力與東南亞最強的泰國和日本拳王互有勝負。
但在七年前的一次護級戰中,師傅失去了右眼的視力。
「對日常生活影響不大,就是有時會分不清遠近。」
師傅講得輕描淡寫,但影響不大也只是指日常生活而已。
對拳擊手而言,距離感幾乎是生命線。
畢竟對方的拳尖與自己下顎的幾公分,就是生與死之間的距離。
在師傅的右眼確診失明之後,他毅然地決定退出拳擊界,在好幾年後開了這家拳館,擔任起教練來。

鄭護身處的這拳館絕對算不上小,除了正中心的標準擂台之外,四周放著的訓練器材由各式不同用途的沙包到不同重量的啞鈴都一應俱全;而難能可貴的是所有器材都是幾乎一塵不染;足見馬頭對拳館的用心。
訓練實戰型的拳手並不賺錢;這在業界裡是公認的事實。
所以大部份拳館在訓練實戰拳手的同時,也得加開不少其他課程以補貼收支。
比起認真訓練拳手,真正能賺錢的是招攬 OL 學員揮灑汗水纖體瘦身的健身室型拳館,教練只需要跟著節拍領著一大班學生隨便揮揮拳;幾十人份的學費就可以袋袋平安。
但馬頭的拳館是其中的異類;馬頭的弟子,永遠不會超過五根手指頭之數。
按他的原話來說,就是「我只教想變強的學生。」
不需要「強」,只需要「想變強」。
這是一種可圈可點的招生方式。
或許正因如此,馬頭門下出了不少冠軍級的拳手。
可是,即使拳館再小,這些年經營下來也絕對不是甚麼小數字;馬頭到底是怎麼樣靠這麼少學生把拳館經營下來的……大概只能歸功於現役時代所存下的獎金了吧?
擂台旁,離剛才示意一回合完結的鐘響剛好五分鐘。
在拳擊比賽中,兩回合之間會有一分鐘的停頓讓拳手休息;而休息一回合加上兩次回合間的一分鐘,正好五分鐘。
拳館的所有休息和練習時間都會以這種三分鐘和一分鐘交替的方式分割,好讓拳手習慣實戰的時間流逝速度。
眼看電子鐘的秒位快要跳到零零,鄭護站於沙包前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在喇叭敲出噹噹聲的同時,開始揮拳。
而師傅則走到鄭護不遠處坐了下來,不自然地搔著眼窩,右眼眼角處還不時輕微地抖動著。
要知道一千次直拳並不是甚麼容易完成的作業,即使是優秀的業餘拳手,打完一千拳,手也酸軟得抬不起來;假如底子不夠厚而硬撐著打完一千拳,甚至會嚴重拉傷筋肉。
鄭護當然很清楚,因為他就曾經因為這樣拉傷過。
但回想起來,鄭護倒是沒有對師傅有點無理取鬧的指示不滿,只是覺得以前不顧身體極限而硬撐的自己有點好笑。
時光飛逝,現在一千拳在鄭護眼中也不是甚麼難事了。

「你來這裡快要六年了吧?」師傅冷不防地道。
「對,」鄭護嘴上回答,揮拳的動作倒是沒有停下來:「再兩個月就要六年了。」
提及這裡,兩人腦海裡不約而同的浮現當年那個下著小雨的黃昏。
「那大概差不多了,你下個星期去參加比賽吧。」師傅道。
「……好。」回答的聲音看似平靜,但鄭護正在擊打沙包的右拳立馬靜止了下來。
在香港,業餘拳擊的賽制為積分制,從一年的四月到下一年的三月,拳擊總會每個月都會舉辦例行賽,參賽拳手會按其勝負數獲得積分,而在年末到達指定分數線的,會以淘汰賽的形式爭奪該年的冠軍腰帶;而所謂的指定分數線,一般而言就是該年度最強的八至十六位拳手。
而這種看起來甚是隨便的賽制有兩個重點。
一是幾乎不含運氣成份,畢竟拳擊總會所配給的對手,一般都是勝率相約的對手;二是雖然機率不高,但相同的組合重新對上也是可能發生的;而復仇戰往往是搏擊運動裡最精彩的賽事。
「只是……現在不是已經八月了?」鄭護反問道:「例行賽都打了四個月。」
「沒事,」馬頭一派輕鬆:「全贏下來的話還是能進決賽的。」
「怎麼?」馬頭輕蔑地笑道:「怕了?想明年一月才打?」
「不,」鄭護笑笑,一記左刺拳全力往沙包轟去,「澎」的一聲嘹亮脆響:「我等好久了。」
從馬頭提出這個建議,到鄭護第一次站上擂台,只是過去了七天。
一般而言,一星期的準備時間絕對是不足的,先不說技術和心理準備層面;對一般拳手而言,實戰的體重通常都會比其自己體重低三至五公斤,但鄭護比較特別,他所參加的羽量級幾乎是他的自然體重,在比賽前不用特地減磅。
但選擇在自然體重戰區作戰的人並不多,因為減輕一個量級的話,會有多少體型上的優勢;而羽量級更加是亞洲戰況最激烈的量級,本來只是求勝的話,避開才是絕對的上策。
但鄭護幾乎是沒經過思考就決定了。
原因很簡單,這是當年師傅所在的戰區。
假如鄭護的自然磅高於羽量級,大概他也會毫不猶豫就選擇調整體重吧。
因為是自然磅的關係,鄭護過磅很順利。
但這僅限於身體狀況的準備而已,精神上的準備又是另一回事了。尤其鄭護從來沒有和任何館外的人對賽過;模擬戰的對手只有同門師兄弟、師傅和一些師叔伯而已。
這很異常。
老一輩的教練訓練拳手的手法一般相當原始而粗暴,就是帶著弟子踢館。
熟悉的、認識的、勉強知道的、硬摸上去的都有,甚至不限於拳擊,踢拳、泰拳,甚至國術也不例外。
這手法原始而粗暴,但是見效——沒有被折斷的,自然就會變強。
可鄭護是唯一一個例外。
即使鄭護本人也再三要求過,但師傅從來沒有批准過讓他參加任何一次館外戰,也從來沒有解釋過原因。
所以,以更精確的用字去講解的話,鄭護從來沒有在擂台上面臨過任何「敵意」。
這使鄭護現下十分緊張,比正常初次上陣的拳手都來得緊張。
他站在空無一人的擂台面前,不知道在想甚麼想得出神。
「好好習慣一下這種感覺。」師傅從後拍了拍鄭護的肩膀,立馬讓鄭護嚇得差點要跳起來,看來他根本沒有察覺到師傅站在他後面有一陣子了。
「很緊張麼?」師傅不禁失笑,他順著鄭護的視線看去,那是仍舊空無一人的擂台;而擂台上散落著斑斑駁駁,大小不一的棕紅色塊。
小的只有一星半點,大的足有拇指肚般大。
有些深得已和淺藍的地蓆融為一體,只剩下一點點棕紅的邊緣外框;也有的仍泛著些許鮮明的暗紅。
那是歷來在上面練習和比賽的人所留下來的血。
「有一點。」鄭護坦然地回答道。
鄭護伸出手,輕輕地刮了刮離他不遠處的一小塊血跡,但血跡早已深深地滲進地席裡面去了。
在自己的拳館裡,鄭護也沒少在擂台上留下血跡;所以令他感到恐懼的不是流血本身。
而是伴隨著流血的落敗。
轉念至此,鄭護便有種難以呼吸的感覺,想像中的敵人也無限地變得高大了起來。
但與此同時,他的心跳加速中明顯有著恐懼以外的情緒。
對於能夠在擂台上揮拳這件事,鄭護有點莫名地興奮。

Thanks for subscri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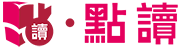
您提供以下所需要的個人資料,即表示您已閱讀並同意《點讀》的《私隱政策聲明》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並同意 《點讀》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以作訂閱《點讀》的電子資訊之相關用途。
如有需要,您亦可以隨時取消訂閱或修改您的個人資料。若有疑問,請電郵至 read@shkpreadingclub.com。